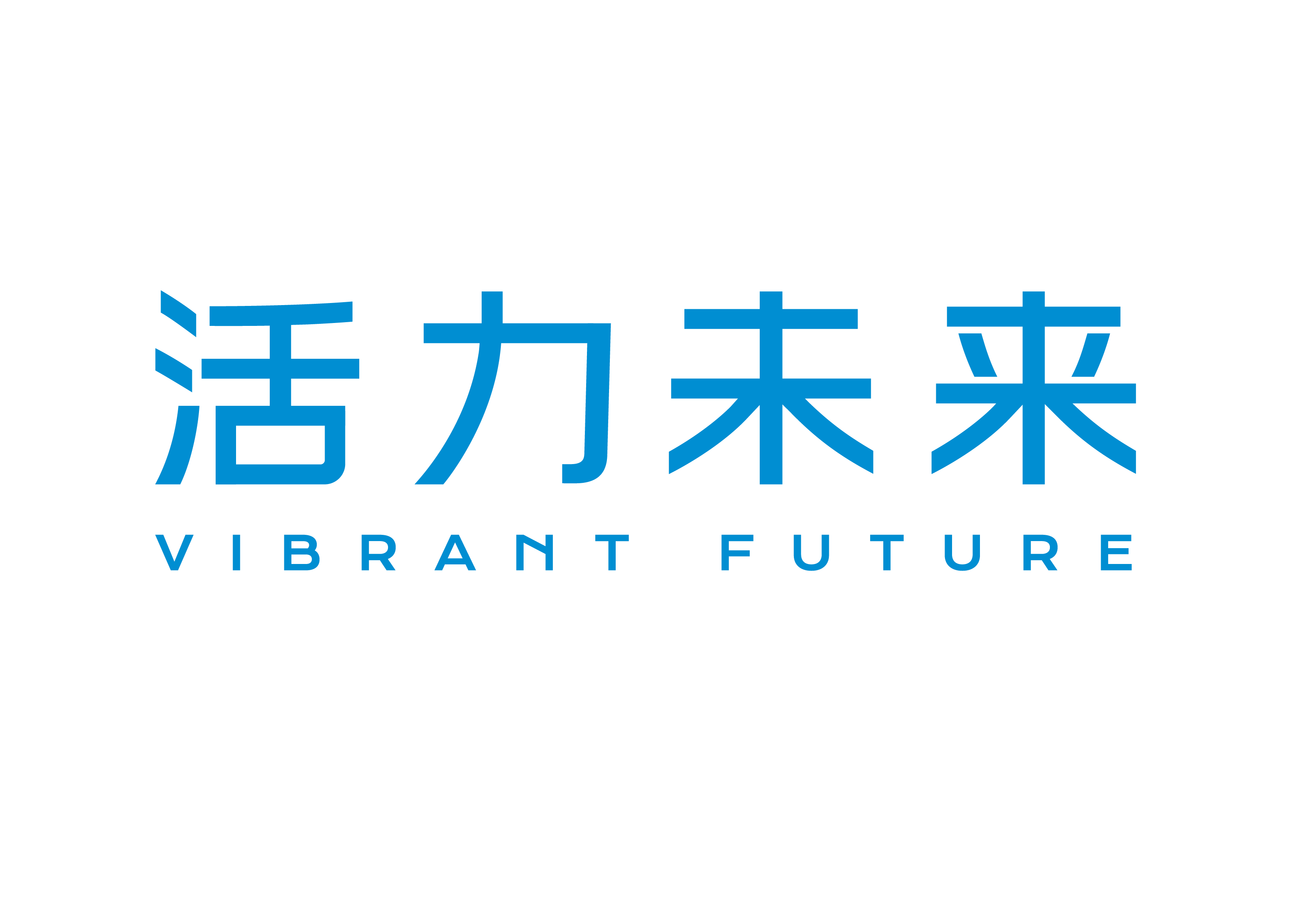|
曹大龙上学记曹大龙上学记 《GATEWAY南方航空》-第264期
雪雁为了儿子能够入读公立小学,提前整整一年开始办证:社保缴纳区和居住证所在区要统一,“克服”城中村房地产所有权的障碍……最后这些证要由居委会审批。幸亏房东等好心人帮了大忙,大龙今年得以进入朝阳区的一家公立小学。
没有劳务费,疯了?
大龙所在的班有35名学生,其中22名是本地生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(以下简称“六普”),中国有近3800万流动儿童,他们随着父母,在城市与乡镇之间迁徙,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,平均每三名儿童里有一名是流动儿童。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。
但矛盾不再是失学问题。2008年,温家宝总理提出“两为主”(以公校为主,以迁入地为主)后,流动儿童的升学率达到了90%以上,其中约205万流动儿童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。“我们接触的,可能一万个流动儿童里面没有几个失学的,其中还有特殊原因的。”蔺兆星说,他是服务流动儿童的“新公民计划”总干事。2011年之后,新公民计划从“有学上”向“上好学”转型。
“再往前推升学率,政府就很为难了。从我们的角度,就愿意为这205万孩子教育质量的提升努力。”蔺说。
他们的切入口是抓教师。“我们的估算是一名教师至少能影响50名孩子,影响教师是公益效率最高的”,蒋海倩说,她在新公民计划中有6年的服务经验。而他们的旗舰项目是每年从全国1400多位民工子弟学校和乡村教师中,筛选出近400位,每学期发放800元“行动基金”。
基金的发放看上去像撒胡椒面儿,只要“符合孩子需求,手段合理”,都有机会通过。其中既有迫切实用的性教育、卫生习惯、交通安全,也有务虚的阅读表演、环保绿植、艺术美劳。钱不多,发放速度倒非常快,从申请至到账只需五六个工作日。这样松散而简单的项目中,却蕴含了教师和社工极为繁琐耗精力的工作。
首先,这800元中没有教师的酬劳。“所以啊,这个项目好在自然筛选,先筛出有意愿的老师,他愿意折腾,不是混日子,更不可能来骗这800。”蔺兆星坦陈,“你想想看,没有劳务费,还增加工作量,是不是疯了?所以,来的人一定是想干点事儿但是手里缺点儿经费。我们立刻给钱,还鼓励他们买好绘本,好教具。”2011年之前,新公民计划主评“金园丁奖”,选出有故事的,“很苦很苦的”教师。在那个阶段,他们与全国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、乡村学校之间形成关系网络,也建立了教师们的信任和意愿。
行动基金的审核标准:“符合孩子需求”“手段合理”也不简单。“比如,一位老师说,孩子的作文表达能力不够,我需要这笔钱给每人买本作文书,我们就不会支持。”蒋海倩说。“孩子需求是在的,但我们认为写作不是靠作文书能写好的,而是依靠大量的课外阅读和观察,才能写出真情实感。”但机构不是简单打发回去,而是向申请人沟通辅导,可以再调整审批。批发后,机构每年还要对孩子回访评估,对教师进行培训、沙龙讲座……都是缺乏“明星气质”的繁琐工作,他们却要一项项落实。
把家庭拽回教育
我问雪雁,如果大龙入公校的证件实在办不下来,她怎么办?她说,“一年前我就是铁定了心,无论如何要把它办下来,办不下来,我一定不会让他在民工子弟小学上学。我应该会陪他回老家”,那就意味着李雪雁将和她的丈夫、小儿子分离。“所以,碰到那么为难我的时候,我都没有退下来,我就跟他说,反正我这个人就这样,你今天不给我办,明天我还来。”
采访时,大龙已经上了一个月的小学,但他并不开心,因为老师“管得太严,谁作业做得不好,就撕本子”。他最喜欢回到活力社区东坝中心的红队教室,李雪雁是这个中心的项目官员,红队教室是她自己辅导的班。在这个民间公益机构的类托管班里,大龙觉得“可以不用上小学了”。
公益机构找到了另一个“上好学”的入口。活力社区在北京和上海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共五个社区中心 ,每年服务超过2000名0-12岁的流动儿童。刚进入社区时,以辅导和托管小学生为主,但发现效果不持续,“孩子半年不来就变了”。“只干预孩子,没拉近家庭,公益效率是打折扣的。所以我们尝试跟家长一起做改变,把家庭拽回到教育里来。”活力社区中国区总干事侯蔚霞说。
但很多父母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,每天忙碌到无法顾及子女教育。生活在城市边缘、经济压力导致大多外来务工家长的教育方法原始而粗暴。“你没见过那些家长宣泄不出来的时候,他把火气发泄到孩子身上……我见过,那个孩子的眼睛是直直的,没有任何表情,”李雪雁停了一下,“很多,”“我跟所有家长一样,经历过很多事情。当你负面情绪很大的时候,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比我弱,我只能把各种各样的压力倒在他身上。”
侯蔚霞说,孩子刚刚入班时,能明显看到有的是有问题的,大部分孩子非常害羞,爱躲着人或者抗拒沟通,而有的孩子性格叛逆暴烈,“这些都是平常家长跟孩子沟通不好甚至没有沟通导致的问题”。活力社区在现实坚壁上找到一个小小的出口:0-3岁幼儿的亲子班。在这个通常母亲能够抽出时间的阶段,“妈妈学会好的方法,更能持续影响这个家庭。”
与社会上的早教班不同的是,亲子班上课时间更频密,而且要求家长参与阅读、游戏;要求家长当志愿者,参与组织读书会等各种活动。最初,这些长时间与社会脱节的妈妈们通常很不自信,但当了志愿者,就不得不跨出去组织、筹备、协调各种事务,“这对她们建立自信,积极的心理建设帮助很大,对未来她的亲子关系非常重要。”2015年,活力社区邀请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朱教授来调查社区妈妈。访谈中,朱教授表示感触太深,“这些妈妈们非常自豪,很多人还要带两个孩子,很累很烦,但她们完全自发地谈论她们的幸福感、成就感。”前两年,李雪雁每回一趟老家就会“纠结一次”,在开发阶段的滨州,有的小学还没毕业的老乡在工业园区里一年能挣8万元,但是只要她一回到北京,一看到大家,“我就很有成就感,有价值感。”
从流动到留守
如果现行政策没有变化的话,大龙6年后还将回原籍参加小升初考试。在北京市教委的网站上,记者查到,目前朝阳区有122所小学,但只有28所初中和17所完全中学,教育资源进入中学阶段后不是一般的困窘,部分孩子甚至从四年级开始就陆续返乡。对于大龙来说,成为留守儿童似乎无法避免。
可乡村不再是终点。在耕地和务农意愿急降的境况下,留守儿童的下一站只有再回城。途径是高考或者务工。而能够考入高等教育系统的留守儿童是很少的。“父母如果没法一起回家,很容易产生亲子关系的破裂。孩子如果缺少稳定的支持,他的能力、知识和观念得不到很好的塑造和锻炼,厌学辍学的比例是很高的。从我们接触的情况,大部分上到初中就念不下去了”,侯蔚霞说。剩下的路只有就业,而初中学历所能对应的通常只是一个高强度、长时间、流动性大的工作,缺少完善的社保,那么孩子就会面临各种安全和治安问题。
如果对流动青少年视而不见,结果会如何?在记者能够查到的上海、重庆、杭州等城市犯罪率中,流动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在20%以上,流动青少年的犯罪率在60%以上。蔺兆星不愿描述这个局面,“我想说的是,如果一个社会不给孩子正常的基本教育,等到成人以后,他看待世界的方式,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,和现在社会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。”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法治……这24个词我都会背,不过生活中我没有特别感受到。”雪雁说。
迁徙,不只是为了财富
李雪雁爱笑,而且笑起来很欢实。更具感染力的是她清晰生动又有亲和力的口才,与刻板形象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木讷迥然不同。
高中时,她为了弟弟能够上大学而休学,跟着爸爸做小生意,来京后与现在的老公一起成立了一家国际快递公司,2008年金融危机,加上管理不善,俩人退出了公司。2009年儿子出生,经济困窘,加上社交圈狭小,让李雪雁在这个城市感受到深深的孤单“只有我老公是我唯一的亲人”。2011年,带着儿子偶然进入活力社区的亲子班后,她从志愿者开始做起,一直到担任这家机构的实习生,2012年在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北师大的培训后,成为正式员工。“我不再只是一个在家里面看孩子做饭洗衣服的人。”
“我在老家可以挣钱,但是没办法让我这样自信,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这么大体现。我跟同学们一起,聊起来觉得我特厉害,尽管有一天我会回老家,是的。”
说起钱,她笑着说,因为开过公司,“也曾经觉得自己是有钱人”,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,大部分国际客户退出中国时,她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:“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国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,从那个时候起,我觉得国家的任何事情都跟我们有关。” |